九龙山的半路凉亭
早时赶路,多凭脚力。一趟两个钟头的路程,走到一半,就会看到一处亭子模样的屋子,或为茅草间,或为砖瓦房,专供行人饮水、歇脚之用。赶路的人们亲切地称其为“半路凉亭”,大概就是古人所谓“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规制的遗存吧。
不过,乡间的凉亭不像现今城市公园里的亭子那样顶角上翘、以柱代墙,它的顶盖跟一般家居的屋顶并没什么两样,周边也有墙体,只是少砌了一两面,一般不设门户,非常通风。早年住小屋,每逢刮大风,屋内的坛坛坛罐罐瓶瓶碗碗叮叮当当地响,母亲老是自嘲:“住在凉亭里,冷在北风里,穷在铜钿里”。
从荷田乡秋田铺谭家外婆家到岩口镇镇上,约莫三十几里路,其间过马家庄、管竹冲、梅塘坳、膝头岭、岩口水库,每经上述地点,就有一座半路凉亭。

幼时随母亲去六都寨镇上大姨家做客,偶或顺道搭一下同村人的拖拉机,多半时间则完全靠双腿赶路。一开始,还新鲜,不觉得累,个把钟头之后,两腿铅似的沉,像跋泥涂一般,渐渐地就落在后头了。母亲频频回头喊:“莫歇!莫歇!前面就是半路凉亭了!”过几天原道返家,母亲又会这样喊。多年以后,每每在学习、工作中心力交瘁、茫然无措时,我的耳畔总会响起母亲当时的喊声,清晰,悠长,绵远,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影影绰绰的半路凉亭。
其实,凉亭内也没多少摆设,几条长长的石凳,一只大大的水缸,缸沿放着两三把竹筒做的水勺,如此而已。乡下人没什么讲究,做事只求痛快,常常一手挥汗,一手抓勺,也不计水的生熟,舀起来便朝嘴里灌,免不了呛着咽着。附近管亭的大叔闻声赶来,急急地往水缸内撒上一把谷皮,谷皮星星点点地弥散开来,再性急的人也不得不吹一口喝一口了。
倘使不赶时间,人们会聚在凉亭中一块纳凉歇脚聊会儿天,种稻栽树啦,下菜秧啦,挑棉苗啦,打麦秆啦,收烤烟啦,剪桃枝啦,牵瓜藤啦,家长里短,说也说不完。在七嘴八舌的描述里,原本单调沉重的地头劳作似乎也变得有趣轻盈起来。
凑巧的话,九龙山膝头岭仙迹亭(中立亭)歇脚的人群里还会冒出几副金嗓子来,即便吊上几句,也大可解乏。那时通俗歌曲尚未流行,人们多唱革命样板戏,一句“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虽说不至于响声遏云,却真能使上岭下坡过往的拖拉机熄火。当时岩口公社文化站在各大队巡回放映露天电影《城南旧事》,主题曲《送别》也随之传唱开来,以后陆续流行传唱的还有《九九艳阳天》、《哥哥你走西口》、《刘海砍樵》花鼓戏小调、《知音》、《月亮走我也走》等通俗歌曲。
记得一个阴天的午后,我一个人徒步经过新田红叶亭的半路凉亭去枫林坪表姐家,不经意间听到有人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下子被击木了。望着凉亭周边一望无垠的竹林麦地,我的心神也随之绵延开来,再也收不拢了。
从秋田铺出来,翻过黑山坎,朝北走上两里路到马家庄,也有一座半路凉亭。暑假夏夜里,吃完水蜜桃回家,手里提着葡萄、黄梨等满满一大袋水果,外婆总要亲自送上一程。说说笑笑,不觉已上岩六大路。母亲劝道:“阿妈(方言,即妈妈),你回去吧!”外婆抚着我的脑壳背,笑眯眯地说:“不要紧,不要紧!”这样劝一阵送一阵,一直走到了马家庄半路凉亭。月色清凉如水,衬出层层叠叠的亭影,原本窄小的凉亭恍惚间舒展开来,悄悄地将我们融化在它的柔影里。外婆像往常一样,从亭子边的一棵桃子树上折下一根桃枝,小心翼翼地别在我的胸前,絮絮地念念有声叮嘱些什么话语。母亲告诉我,桃枝能避邪,当心掉了。就这样,外婆朝南走,母亲和我朝北走,留下半路凉亭静静地守望着对方的方向。因为酷暑伏天里白天赶路天热人透不过气,夜晚趁着月光赶路凉快。

佛经里说,世间万物有成必有坏,半路凉亭亦然。永久牌自行车、嘉陵牌摩托车、邵阳果园牌农用车渐次进入乡下人的生活之后,一度繁忙热闹的山间凉亭慢慢地破落冷清了。亭顶漏了,没人补;水缸溢了,没人匀;石凳裂了,也没人修。在一个又一个疾驰如飞的日子里,人们似乎越来越关注目的地,越来越忽视绵延的路途及两边的风景。
每回开车掠过家乡九龙山那些打满了岁月补丁的半路凉亭,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凝视一番。小儿说,他仿佛听到了九龙山半路凉亭的呓语:“慢慢走,欣赏啊!”可是,这样的声音还有多少人能听见呢?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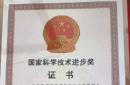


 湘公网安备 43010402000822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40200082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