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花瑶“讨僚皈”——说说隆回花瑶的历史(三)
千年花瑶“讨僚皈”
——说说隆回花瑶的历史(三)
林子
《雪峰瑶族昭文》是晚清瑶族秀才记述本民族口述史的文本,所以出现时间、地点等的误差,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应将《雪峰瑶族昭文》与官修史志资料结合一起来看花瑶的历史。

自明清以来,花瑶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花瑶与官府抗争,争取自己生存权益与生存发展空间的历史。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在治理湖南少数民族地区时,逐渐调整控制与管理方式。
从纯粹的镇压逐渐过渡到安抚教化,到清中期,开始强化儒学教育、鼓励少数民族参与科举考试,有效地增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融合与政治认同。隆回花瑶地区也随着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治理花瑶地区的策略转变,儒家文化极为深远地影响到了花瑶民族的政治、族群与文化。

据花瑶内部流传的手抄本历史资料《雪峰瑶族诏文》的记载,花瑶先民其所经历的不断迁徙的历程,不仅体现出其“性喜迁徙”、“富有移动性”的山地民族特征,更体现出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极其艰难,加之与外部政权、不同族群之间处于接连不断的冲突与战争,导致花瑶的生存空间不断萎缩,从而被迫迁徙。
面对这一地区的复杂情况,明清两代的中央政权在进行治理与管控时,采取了许多并不相同的策略,并通过不断强化儒家文化的渗透与示范效应,有效地增强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与社会稳定。

从明隆庆《宝庆府志》中可以看到,明代宝庆府地方防御体系,主要以瑶苗二族为重点防范的对象,该府志中所涉及的诸多武将的简单传记,其功勋卓著者往往与弹压苗瑶之间的战争相关。
明代以来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相对抗的状态,也集中地体现在了花瑶所居住的地区,如清同治年间编撰的《溆浦县志》“兵防”中,在列举了宋以来瑶族人的反叛,以及与外族人之间的诸多战争后,直接提出了如下论断:“《陶志》以瑶防、兵防分为二,以溆之宜防者莫如瑶也。”从而将“瑶防”的概念从兵防之中单独提出来,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防卫对象。

不过,即使在双方对抗相当明显的明代,在这一更为宏大与明显的族群间的抗争史之外,依然存在着另外一条更为隐蔽也更为细微的族群间关系演进史,那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所发生的或民间、或官方的交往与互动。
虽然明代湖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与对抗仍然时有发生,但中央政府对于这一地域的控制日渐强势、成熟,汉族人也从人数、地理范围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以此为背景,瑶汉民间的交往与互动,也开始出现了不一样的发展趋势与格局。
清道光《宝庆府志》“卷百二十四 任侠”就记载了这样一位在明代时就定居瑶地,并教化瑶民的奇人:
“萧元辉,武冈人,豪迈有干略。……先是,小坪多瑶僮种类,鸟言卉服,斑斓侏离,自汉唐以来,更居化外,或 劝元辉当择地而蹈。元辉日:是亦人类也,乃不可共处耶?日率其弟元隆元喜,劝谕瑶人开垦种植树艺,兼为讲说礼义仁让,使知父子之亲,夫妇之别,睦姻任恤之谊。又使其子弟教瑶民子弟读书识字。瑶民乐之,渐知向化。”
这是一篇很显然站在汉族人的立场所撰写的人物传记,将汉与瑶二者进行了明确的对立。
一方面,从心态上强调汉地优于瑶地,故而当汉族人迁徙时,要“择地而蹈”,远离瑶地;
另一方面,从种族上强调汉族人优于瑶族人,故而会有“是亦人类也,乃不可共处耶”的自我辩护,换言之,在当时很多汉族人的心里,瑶民与汉民并不是一类人;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强调汉文化优于瑶文化,故而当以汉文化教化瑶民时,“瑶民乐之,渐知向化”,这样一种强调从文化上教化并改造瑶族人的思路,事实上也是居于强势地位的汉族人一直期望做到的事情。

在明代这位奇人或是与他类似的人这里,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除了萧元辉这样的奇人之外,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为了有效控制并同化瑶族人,同样采取了多种方式,也付出了诸多努力。
其中,通过有效分化瑶民,在瑶民中培植更为亲近中央政府与汉族人的所谓“熟瑶”,以此来钳制甚至控制其他瑶民,从而形成新的被中央政府所掌控的瑶汉间关系的方式,无疑是所有策略的重中之重。
明代中央政府的相关做法,在清道光《重辑新宁县志》“卷十五 苗瑶”中就有如下描述: “(明)景泰辛未,知县唐荣奏徙县治招抚城步瑶人,给田世住,分为八峒,把守各隘瑶路,号为熟瑶。择峒丁有能干者,县给帖,命为峒长,俾自约束。沿至皇清,相安无事,每年纳本色粮无差。”这样一种通过在瑶民中寻找并培养更为亲近汉文化与中央政权,并以此钳制甚至管辖其他瑶民的做法与努力,并不是明代君臣所创,而是从南宋时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从清同治《武冈州志》“卷五十三 峒蛮志”中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早在南宋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抚使赵彦励就在上书中提出了“以蛮民治蛮民,策之上也”的说法,其建议也获得了当时皇帝与朝廷的采纳。
此后,这样一种通过给予更为现实的政治特权与经济好处等方式以培养更为亲近中央政权与汉族文化的“熟瑶”,实现钳制、管辖不服教化、远离汉族中心的“生瑶”的政治性努力,成为历代中央政府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策略之一。
除了上述“分而治之”的策略之外,到清代中期,中央政府还做出了更为务实与可行的制度性努力,通过鼓励少数民族学习儒家文化,参与科举考试,实现了将瑶族精英们吸纳到政府体制之中的目标,这样的做法无疑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强了对中央政权的政治认同感。

清道光《重辑新宁县志》“卷十五 苗瑶”中称:“(清)瑶编能读书通文理者,应试岁科,取进二名,名瑶生。雍正十年更名新生。设义学两所,……声教日开,学额递增三名,应试者几百人。”
此外,清同治《武冈州志》“卷五十三 峒蛮志”中也对这一状况进行了描述:“我朝声教四讫,瑶童得与考试,给衣衿,其岁考所取 瑶生,仍与生监,一例乡试。”
而关于瑶族学生的称谓问题,清同治《溆浦县志》中也进行了辨析,在清乾隆二 十一年之前,有所谓“瑶生”、“瑶童”、“瑶学”等称谓。

此后,依照黔(贵州)省的规矩分别改为“新生”、“新童”、“新学”。清初以来所进行的这样一种加强对瑶族地区的文化、教育的普及力度,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且单独为瑶族人留下功名名额的做法与努力,无疑为他们改变自身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机会与 可能,也从更为长远的角度上重塑了瑶汉之间关系的整体格局。
花瑶人逐渐进入到汉族人的政治体制、日 常生活、思维方式之中,开始像汉族人一样处理日常事务,如乾隆五十年《续增城步县志》“卷一 民俗”中复者,今则控诉待质矣。士彬雅,农克勤,讳蛮之名而处汉之实。其风俗不大径庭也。”

通过历代政府的不懈努力,到清中晚期,中央政府与汉族人对于瑶民的教化与同化努力,获得了全新的进展与成就,而此时的瑶汉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格局之中。
清道光《重辑新宁县志》“卷十五”中,对这一新的瑶汉之间状况进行了如下描述:“新宁峒瑶属宁者为熟瑶,属他邑者为生瑶。……(至清中期)向之目为瑶者,群耻其号,人情风俗,悉与县同,所谓民瑶是也。”根据瑶民与汉民之间差异程度的递减, 关于“瑶”的称谓,也被进一步区分成为了“生瑶”、“熟瑶”、“民瑶”,越往后,瑶汉之间的差异越少,汉族人对于瑶族人的教化与同化策略就越成功。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武冈等地,清同治《武冈州志》“卷五十三 志”中也对“瑶”进行了如下区分:“有山瑶、民瑶之分,民瑶与夏人杂居,服食居处冠婚丧祭,具与民同。……其山瑶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与巴渝同俗。”
此处所谓“民瑶”与“山瑶”的区分,同样是建立在瑶民与汉民之 间相似程度的基础之上的。
可见,到清代中晚期,“民瑶”已经不仅从语言、文字、习俗、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与汉民相差无几,此即《武冈州志》所谓“具于民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待自我族群特征的心态上,也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更是出现了《重辑新宁县志》所谓“向之目为瑶者,群耻其号”的奇特现象。

换言之,此时的“民瑶”对于自己所属的“瑶”的族性,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厌恶与自我反感的心态。
这也充分反映出清代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儒家教育、鼓励科举考试,在实现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方面,所取得的明显效果。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
相关内容
- 隆回麻塘山仙石寺 为元末明初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而建(2017-09-18)
- 忆隆回农民“发芜”走过的“长征”路(2017-10-31)
- 那些你不知道的隆回茶文化,曾经也有驰名中外的名茶(2017-10-31)
- 隆回文人用故事记录即将消失的行当——石匠(2017-11-03)
- 梳理毛泽东与隆回人的交集(2017-11-14)
- 隆回人与辛亥革命(2017-11-30)
- 隆回祁剧团的兴衰(2017-1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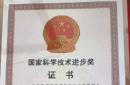


 湘公网安备 43010402000822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40200082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