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夷奇人刘培一
新宁县,古时候称为“夫夷候国”,以后改为“夫彝”、“扶彝”、“扶县”,宋朝初年改为新宁县,夫夷候国以江为名,一条名叫“夫夷”的河流横贯全境,县城设在河流的中部,依山傍水,名为“金石镇”。
清朝末年,新宁楚军在这里发起,历时十几年,纵横数千里,在国内平乱和抵御外侮的数百次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成就了几百位战将。其中最著名的有安徽巡抚江忠源、兵部尚书兼直隶总督刘长佑、头品顶带,两广总督兼南阳通商大臣刘坤一。好男儿当驰骋疆场,建功四方,青史留名,万古流芳。可偏偏有这么一个人,视功名如粪土,视官场如茅坑,不做红花甘当绿叶,一心一意协助兄长成就一世英名,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家乡的战后重建和民生工程上。他就是刘坤一的弟弟刘培一。
刘坤一同母兄弟一共有四人,分别为坤一、培一、瑞一、傅一。刘家世代都是读书人,他父亲以教书为职业,没有田产,也没有商铺,家境清寒,生活艰难,为了让兄长和弟弟们安心读书,也为了让继母生下的一大堆弟妹们能顺利成长,刘培一很小就接过家里的重担,为母分劳,为父分忧。他十四岁就跟随堂兄学做生意,他头脑灵活,不怕苦,不怕吃亏,很快就上了路,然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滾越大,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把一个缺衣少食的家庭经营成了新宁县数一数二的大家族,让他们家成了与“余庆堂”齐名的“光厚堂”。
刘坤一是在父亲死后那一年墨绖从军的,一生纵横疆场,沉浮宦海,成了国之栋梁,朝庭重臣。
其实刘培一比他成名更早,湘军鼻祖江忠源刚刚出县作战的时候,就把不满二十岁的刘培一请到身边为他出谋划策。刘培一虽然读书不多,也没有作战经验,但他在商场摸爬滚打数年,俗话说商场如战场,他的建议和调度屡屡出奇制胜。江忠源对他言听计从,但是江忠源是一个战争狂人,一心报效朝庭,求胜心切,放纵部下胡作非为,江忠源本人好杀成性,对于俘虏和被裹胁的女人也是杀无赦。当时,江忠源和曾国藩齐名,江忠源人称为“江屠夫”,曾国藩被称为“曾剃头”。刘培一规劝过几次,江忠源没有放在心上,反而认为刘培一幼稚,不知江湖险恶,那些老兵油子们对刘培一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早就看不起,认为他是来打秋风的,来喝兵血的。刘培一本来就是来客串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向江忠源告辞,谢绝了江忠源丰厚的馈赠,毅然回到了家乡。后来,刘长佑和李明惠掌握兵权的时候,多次请他出山,都被他婉拒。他的军事才能过了十多年才得以展现出来。
刘瑞一,字立藩,后改名为刘镇,是刘坤一的二弟,他从小就被誉为“神童”,十几岁就中了秀才,他在父兄的督促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自信求取功名如探囊取物,可是屡试不第,这更激发了他的疯劲,废寝忘食,常常通宵达旦。久而久之,疾病缠身,最后那次在岳麓书院考试时吐血不止,只能退场,在湘潭的路上饮恨而终,时年二十八岁。
噩耗传到广西时,正是刘坤一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正所谓爱之深责之严,他每个月都要写信给弟弟,督促他用功,哪知这些书信却成了弟弟的催命符。弟弟的死讯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十多年的不停征战,让他暗病缠身,无数次的死生遭际使他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病来如山倒,刘坤一病倒了,病得不轻。
刘培一听说兄长生病,连忙昼夜兼程赶赴广西。其时,刘坤一因军功升任广西布政使,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时把楚军的指挥权也交给了他,他把楚军改名为“新楚军”。表面上看他军政大权一手抓,实际上他是被架在火炉上烤,焦头烂额,苦不堪言。不管楚军也好,新楚军也好,都是一支民间队伍,朝庭不负责粮饷,过去当兵称之为“吃粮”,俗话说“一日无粮千兵散”,刘坤一名为布政使,上有巡抚和总督,他根本没有权力调度钱粮和正规军。广西是太平天国的发源地,是战争的重灾区,十多年来,战火一直不断。刘坤一接手楚军以后,屡屡出师不利,连吃败仗,对手是一股悍匪,占据浔江和大山,为害多年,他们深得游击战的精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刘坤一被搞得精疲力竭,狼狈不堪。
刘培一来了以后,亲手为兄长煎汤熬药,好语劝慰,经过几个月的调理,刘坤一身体渐渐恢复。刘坤一知道情势紧急,自己无力回天,决心以死报效朝庭,他用计把刘培一送回家去。刘培一走到半路,忽然醒悟,马上打转,刘坤一又要自己的好友当说客,用伍子胥兄弟的故事来打动他,说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他要尽忠,要弟弟尽孝。刘培一走到哥哥面前,大声驳斥他:“男子汉大丈夫面对强敌怎么尽说喪气话,自古人定胜天定,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必定能反败为胜。”他深入兵营,与士兵同甘共苦,又极力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了解敌我双方的实情,精心谋划进攻战术。经过三年血战,剿灭了最大的劲敌。期间,最艰难的时候,每个士兵每月只有九斤谷米和十几斤红薯,刘培一乐观亲和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深深赢得士兵们敬佩,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刘培一同生共死。刘坤一因为避嫌,没有把弟弟的功劳申报朝庭,广西巡抚上疏极力赞扬刘培一,并且把刘坤一隐瞒的原因也让朝庭知道,朝庭升任刘培一为候补知府。三年后刘坤一升为江西巡抚,两广总督认为临阵换将不利,让刘培一统领广西的军队,继续清剿广西的残匪。又是四年的鏖战,广西全境终于恢复太平。战胜之后,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七年的军饷得到补偿,有功之人也得到了封赏,面对巨额的钱财,升官的诱惑,总督的挽留,刘培一选择了告退。他对总督说:“侥幸取胜,实属意外,全身而退,真是万幸。”他像来时一样,一个包袱,一把雨伞,一个人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刘培一到家不久,他昔日的部下凑了三千两银子给他送来,让他到京城去补一个实缺,他有道台和按察使的衔头,在吏部已经挂了几年的号了,有两广总督的保荐,有硬梆梆的军功摆在那里,皇上和太后也多次对他嘉奖,谋一个实实在在的肥缺是坛子里摸乌龟——十拿九稳。刘培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对来人说:他没有经天纬地的才干,不能独立地实现自己的抱负,更厌恶官场中的习气,一旦陷入,进退两难,无异于自投苦海。刘培一不想为世俗的名利所累,也不是想做超然脱俗寄情山水的世外高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只想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他是刘家的当家人,也是兄长刘坤一的坚强后盾,刘坤一为官几十年,不贪不占,清正廉明,离不了他的警醒和燮理。刘家在他的治理之下,人人安居乐业,无一人仗势欺人,作奸犯科。让刘坤一的敌手们找不到任何攻击的理由。
刘坤一在担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兼署海关,完成上缴任务后,结余二十多万两银子,按照常例,可以归自己所有,他犹豫不定,写信征求刘培一的意见,刘培一态度鲜明,“上交国库,充作军饷,不留分毫。”俗话说“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世上有那么多的人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最后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局面,后悔不迭,噬脐莫及,他要让兄长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那以后,刘坤一再不对金钱动心动手。
刘培一不是脑袋进水,也明白“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现实,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事实上他是一个很会挣钱的生意人,用现在的话说是“理财专家”。前后对照就可以看出刘培一的能量,因为家里穷,他十四岁就辍学经商,他结婚的时候,唯一的新家俱是一只竹灯盏,短短十几年,他家就成了与“余庆堂”齐名的“光厚堂”,这里固然有刘坤一的因素,但没有刘培一的经营,充其量只能够成为一个土财主。新宁县因军功升官发财的有上千人,四品以上的官员就有两百多人,但没有一家有刘培一的成就,有的吃喝嫖赌,挥霍一空,有的不善经营,坐吃山空。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很多人过不了齐家这一关,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国家是由一个个家庭和家族组成的,家庭不稳固,哪来的天下太平。刘培一不但把自己的小家治理得和和顺顺,更把金石镇的五个刘姓人家“齐”成了一个大家,在崀山石田修建了“刘氏宗祠”,合成了一个“金城房”,购置族田族产,安置贫困无业的族人,所得收益除用于正常开支外,余下的积蓄下来,以备度荒救急。族田由原来的五百石(担)租逐步增加至一千石(田亩面积以收入租谷计算,有四六开,三七开,五五开,六担租谷算一亩田)。每年冬至之日,全族人齐聚宗祠,刘培一带领大家一起温习族规家法,对良善勤奋的家庭给以嘉奖,对懒惰顽劣之人施以惩戒,对遭受灾难和鳏寡孤独的家庭给以救助。刘氏宗祠落成的时候,慈禧太后亲笔题写“根深叶茂”四字,差人从京城专程送来,至今,这块牌匾依然悬挂在宗祠里面。
诚然,家族里面的大事都是刘坤一出钱刘培一出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何况是朝庭倚重的总督和南阳通商大臣,出任的更是富得流油的两广和两江。钱财由刘培一经手,刘坤一一百二十个放心。刘家先后修建了“光厚堂”,刘氏宗祠,学宫,庵院,义仓,义庄。在刘培一的建议下,刘坤一拿出二十万两银子创建了忠义祠,修建忠义祠是为了纪念楚军阵亡的将士,以前只有一部分依附于江忠源的忠烈祠,新宁楚军不是朝庭的正规军,只有有功之士才能得到封赏,当兵吃粮的大多数是穷人,在战场上,有很多是病死,饿死,伤残致死或离奇失踪,他们死后,遗下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和年迈的高堂。刘培一把他们一一造册,设立牌位,春秋祭祀,凭吊缅怀。刘培一又逐家逐户访贫问苦,对有劳动能力的就给他们置办田产,让他们自食其力,对没有后人的老人就养老送终,对未成年的儿童全部接到学宫中免费教育。
崀山石田有座佛顶山,那里有座庙,庙旁边有一间私塾,刘培一感念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从那里负米养亲,如今那所私塾已经凋敝不堪,他拿出钱粮整修庙宇,扩建学校,免费给穷苦人家子弟就学,让钟鼓之声与朗朗书声交相应和,使刁蛮之风潜移默化。(这座学校旧址即今崀山中学)
过去,穷苦人家无力抚养多生儿女,弃婴已成惯例,刘培一出资创建育婴堂,收养被弃婴儿。又创建养济院,收留无家可归的残疾病废之人和孤寡老人。
天花,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病毒,侥幸存活之人也会在脸上留下深深的疤痕,这就是民间说的“麻子”,俗话说“十麻九狠”,指的是这种人的变异扭曲心理状态。刘培一出资两千两银子,创办了“牛痘局”,这是新宁县第一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机构,为民造福,破了天荒。
刘培一出外时,见到年老之人售卖粗重之物,不管家里需不需要,都是一律优价买回。看到别人因为欠债而吃官司时,总是慷慨解囊,代人偿还。穷人最怕打官司,而那些衙役隶胥们则最喜欢无事生非,尤其是人命官司。吃了原告吃被告,连远亲近邻都要不分黑白地扯上是非,涉嫌连坐。俗话说“十堂人命九堂奸”,有奸情就有隐私,为了脸皮,只好破财消灾。刘培一同相好的富户协商,带头拿出一千两银子,一时募得数千金,作为专用基金放在钱庄里生息,用息钱支配衙门中人的车马费和脚力钱,实报实销,不得冒领,也不得另外渔利。由本县有名望的士绅负责监管。从此,衙门中再无鱼肉百姓之事出现。
刘培一没有当官,却比县官更操心县里的事情。同治年间,县里出现饥荒,尤其长湖村最为严重,一村之中几乎不冒炊烟,刘培一根据各家各户的人口多少,借给钱粮,不要借条,第二年丰收以后,大家都来归还,刘培一问明各家实际情况之后,只收本钱,不取利息。光绪十二年,县里遭受旱灾,米价飞涨,因为买不到粮食,西北两乡饿死很多人,刘培一先是把自家积蓄的米谷平价售出,然后又从外地购回数千石稻谷运到西北乡出售,按收购价销售,自贴人工和运费。两乡之人全赖他活命,被人称为活菩萨。刘培一是好人,但不是滥好人,对于那些因抽鸦片或嫖赌而破家之人,即使看到他活活饿死也不会施以援手。
光绪七年,(1881)刘坤一贬官归家,那是刘培一最开心的时光,兄弟连床夜话,追忆血雨腥风,缅怀阵亡战友,感悟仕途迢迭,扼腕国运多艰。兄弟带头纂修县志,增修金城房族谱,一起风光体面地为继母蒋太夫人送终。光厚堂如今儿孙满屋,宾客盈门,不适合静养,刘培一陪着兄长四处踏看,在教场坪选中了一块地,(即今新宁一中)这里面朝金子岭,紧邻夫夷江,日看山间云舒云卷,夜听两岸蛙鼓涛声,是一个绝佳的修闲所在。刘培一为哥哥在这里构建一座庄园,让哥哥颐养天年。两兄弟一起栽下了数十株广玉兰,一百多年过去,至今仍然年年繁花似锦,笑傲风霜,承载着兄弟之间血肉相连的手足深情。
刘坤一在家九年,尽享天伦之乐,也陪着弟弟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里程,刘培一背生痈疽,拒绝治疗,谈笑欢歌,一如继往,视死如归,终年五十七岁(1833——1890)。刘坤一在料理完弟弟的丧事后,接到了官复原职的圣命,十二年后,在南京逝世。
刘坤一没有儿女,弟弟刘瑞一也没有儿女,老四刘傅一有一子名刘能约,刘培一有三个儿子,分别为能继,能缉,能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刘培一将老二刘能缉过继给刘瑞一,老三刘能纪过继给刘坤一。至今,光厚堂仍然英才辈出,群雄济济,余荫绵绵。
本文编辑:铁打的宝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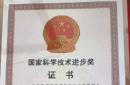


 湘公网安备 43010402000822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402000822号